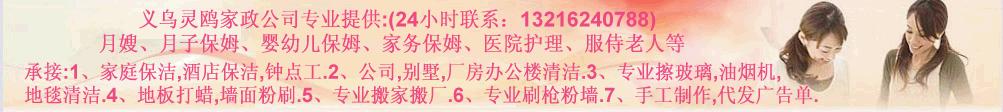|
房向東 海峽文藝出版社社長
前些天,在全國政協(xié)會議小組討論中,著名導(dǎo)演馮小剛呼吁恢復(fù)部分有文化含義的繁體字,并增加到小學(xué)課本里。馮小剛認為,這不會給孩子增加過多的負擔(dān),只會讓孩子更多了解漢字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。
其實,這是老調(diào)重彈。前些年,也是在政協(xié)會上,宋祖英、郁鈞劍們也曾建議,小學(xué)要增設(shè)繁體字的教育。
學(xué)習(xí)文字是為了接受知識,傳播知識,文字具有工具性。一般說來,工具越簡單,越容易被接受。電腦也是一種文化,電腦是日新月異地進步著,電腦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,就是操作越來越簡單,正是越來越簡單,所以越來越普及。我們不能說,為了弘揚電腦文化,我們在用奔5的同時,還要進行奔2的教育。過去的東西很多也就過去了,只要一些專業(yè)人士懂得的東西,不一定大家都要懂,更不必孩子都要懂。小學(xué)生課業(yè)負擔(dān)重,本來就夠煩的了,如果采納了他們的建議,那真是煩上加繁!如果讓現(xiàn)在所有的學(xué)生都去接受繁體字的教育,推到極致,學(xué)校應(yīng)該進行甲骨文的教育了。
前些年,我在《參考消息》上不時看到這樣的報道,香港人、臺灣人如何地喜歡簡體字。臺灣和新加坡都有簡體字的報紙。我接觸過若干臺灣人,也與他們通過信,他們也是簡體字和繁體字夾用。《參考消息》曾報道,記者拍到臺灣名人蔡英文的說話提綱,上面用的也是簡體字。說起理由,無非是寫字快,方便。
寫一千個簡體字,估計比寫一千個繁體字要節(jié)省三分之一的時間,如果每一個寫字的人累計起來,全國該節(jié)省多少時間啊!具體的個人學(xué)字,學(xué)一千個簡體字,也要比學(xué)一千個繁體字快了許多。簡體字在掃盲工作中,可謂立下汗馬功勞,說是頭功也不為過。
字從復(fù)雜到簡單,并不是在公布了簡體字以后,文字是伴隨著歷史的進步越來越簡單,內(nèi)含越來越豐富的,最早的象形字有的簡直就是一幅圖畫,先人們費盡了腦筋,才有了今天這么簡約、干凈的文字。我們某些時代的歌者,打著弘揚傳統(tǒng)文化的大旗,要把先人的智慧,要把無數(shù)文字工作者辛勤勞動的結(jié)果給抹殺了。
唱的比說得好聽的人,卻是特別喜歡繁體字。標榜愛惜繁體字,似乎自己是一個很有文化素養(yǎng)的人,不是只會拍電影、唱歌。可是,我們一些很有文化的人,甚至對繁體字、古文字極有研究的人,卻是極力主張文字改革,簡化漢字,正是他們不遺余力地推動,才有了今天的簡體字。這也是歷史,而且是離我們不太遠的歷史,我們也不應(yīng)該忘記—
譚嗣同、蔡元培、吳稚暉、胡適、陳獨秀、瞿秋白、魯迅都極力推行漢字改革。語文學(xué)界的“大師”和“宗師”呂淑湘認為,“電子計算機是漢字的掘墓人”,“漢字行將就木”。先賢的言論不無偏激之處,但是,我認為這是歷史的先聲,正是他們對以繁體字為承載工具的漢字的激烈批判,才有了今天為國人所接受的簡體字。正如魯迅所說,一個不透氣的黑屋子,你如果只說開窗,衛(wèi)道者們是絕對不會允許的,你要高喊把屋頂給掀了,他們才勉強同意你開窗。
要捎帶一說的是,學(xué)校的教育內(nèi)容有其科學(xué)體系,有其相對的穩(wěn)定性。課堂不是菜籃子,扔進去的都是菜。這些年,除了“繁體字進課堂”外,還不時有“京劇進課堂”、“書法進課堂”等等。毛澤東喜好詩詞,未必要求學(xué)生都要學(xué)填詞;鄧小平喜歡打橋牌,沒聽說橋牌進課堂。
義烏靈鷗家政服務(wù)公司:專門提供家政、月子護理、育嬰師、保姆、專業(yè)陪護、服侍老人、醫(yī)院護理、鐘點工、家庭公司保潔、搬家等服務(wù)。 |